《须臾记》
深冬。已好久不和任何人联系了。
一个人呆着。
听戏,写字,习书法,发呆。整个冬天,风都很大,雪亦多,轻易不下楼。偶尔去楼下爱芬超市买些菜,和她聊聊湘菜做法,她是湖南人,每炒菜必放小米辣。她教我做辣椒酱——把小米辣剁碎,放上盐、白酒、糖……这种辣椒小巧灵透,红通通的,但辣起来惊天动地。在湖南和云南都疯狂的吃过,胃里热烈,但不灼。
听戏,听老戏。三四十年代的老伶人唱段。程砚秋的《春闺梦》,孟小冬的《搜孤救孤》,那声音穿在 钢丝上一般。恍惚间,以为是三十年代的旧人。特别是孟小冬,一点雌音全无,铿锵之下,尽是悲声。那悲声经了时光沉淀反而更有别样妩媚,女人一旦有男性的铮铮,反而妩媚更烈。
亦听少春先生的“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底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派遣,荒村沽酒慰愁烦。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他亦是余叔岩的弟子,男伶中,比他长相奇俊的人几乎没有。我的同乡。霸州人。他眼神中有复杂的悲欣,五十几岁便去世,最好的时光没有到来。有的时候,人到晚年嗓子会更奇妙。声音老了,心态老了,那味儿也许倒出来了。比如黄少华。
我是通过黄少华迷上的荀派。
之前是抵制荀派的。荀派在我印象中是薄俗粉腻的,那粉腻又是略微贱的,所以一直不听荀派。
但重阳节在长安大戏院突然听到黄少华,她已然八十岁,流落江湖,多年不唱了。那天,她唱了两段。
第一段是《绣褥记》。
“顾影伤春枉自怜,朝云暮雨怨华年,苍天若与人心愿,原做鸳鸯不羡仙。”她那个“春”字唱出来,绕梁三日,一波三折……刹那间眼泪喷涌而出!这才是荀派,如此妖如此媚如此让人不舍。听得呆了过去,顾不得鼓掌,顾不得拭泪,心里怦怦跳着,像寻着了那初恋,居然不能自持。
第二段是《玉堂春》中《嫖院》一场。多少人把玉堂春唱成了一个轻浮浪荡的妓女,但她把玉堂春唱成这样情深义重为爱情飞蛾赴火的女子:“公子不用亲笔信,叫人此事好担心,轻移莲步出院门,上了香车攒路行,道路不知远与近,我看望公子不见身,苏三心内拿不稳,苍天佑我会情人……”最后一句“苍天佑我会情人”时,唱得人百转温柔肠,八十岁的女人,把十八岁的女孩子的娇俏唱得从容、干净、动荡、缠绵!你叫我如何不迷恋她。
下载了视频,就这样听她,一听一天。
仿佛亦是苏三或那痴情的女子,在她的唱腔下不知所矣。

亦会练习书法。
初临褚遂良、欧阳询,开始是喜欢的,再临,觉得瘦、薄,而且女气。书法一旦有女气,就没有凛凛之感。在西安碑林,看到颜真卿时会透不过气来,只在那一块碑前有那样强的气感。他的字是带了兵的队伍,一个个杀将过来,每个字都是万里长城,每个字都带着鬼气和巫气。欲罢不能。西安博物馆的小孙从小临颜真卿,整个人看上去有兵气,她不像女子,倒似是兵马俑出来的将士,铁骨中柔肠分明。我与她惺惺相惜,好得竟然半日不说一句话,但山河浩荡之声,彼此清晰明了。
又翻那些旧贴。还是喜欢王羲之。他怎么会写那么好。这不是天赋,亦不是勤奋,这真是上天厚爱这个人。后来的人并不比他吃得苦少,总是笔下少了那份从容与淡定。他有行云流水的不紧不慢,有些人的字,心态流露于字上,一笔一画全是讨好,或者吃力的想诉说什么,可是王羲之不是,他只顾他自己的情绪。这些字是他的乖巧情人,臣服于他的安排,心甘情愿的倒在他的笔中。
临他的《圣教序》,感觉笔墨之间的欢喜。行书可真好!一个中年男了的挥洒自如一般,楷书还是少年,处处拘泥,草书太狂放了,个性外露。只有行书,是中国文化中的太极,可松可紧,外圆内方。它应该重时就浩瀚、豪迈、壮丽、刚烈,应该轻淡时就平静、清淡、化繁为简……那挥洒是半梦半醒之间的,是你知我知的。它亦狂,可狂得有度有法,它亦收,收得那样从容跌宕。这样的冬天,我在宣纸上铺张浪费着感情,毫不吝啬。
在少年时,爷爷独处一室,陪伴他的只有笔墨纸砚,他的被子是不叠的,床上摊着刚写过的字,屋内阴暗,笔墨的香气犹如鬼附体,缠绵在他的晚年我的少年。那时我不过十岁左右,和其它人一样笑他痴。小镇人道他是书法魔症了脑袋,完全没有天伦。别人说笑他时,我以他为耻。总是快速逃开。他对于书法是着了魔似的,除了书法,还是书法。
他除却书法一无所有。他与奶奶分居,与孙子孙女不来往。亦不开玩笑,假如有人和他说书法,他便愉悦。并与之交往。他没有别的任何话题。在八十年代,他显得那样孤僻与格格不入。这在当时是让全家略微显羞愧的事情。连父亲亦觉得他异类,说少时爷爷逼他练书法,他便逃跑,但爷爷去世时父亲拿起笔来,一写就是那个体儿那个味道。父亲临《柳公泉玄秘塔》,犹如神灵附体。写得亦是从容,流水一样的宽厚。父亲把原稿交我保存,只说他百年之后给我留一份念想,他说得从容,我听得惊心。
十八九岁去石家庄读书,同学徐习书法,每日必写。好多女生围着他,看他写字。我并不在意。那时正是青涩而文艺的少女,看那些厚厚的外文书,哪里在意中国文化的好?但他逼着我练了硬笔书法,日后写了一手漂亮钢笔字,不由感叹甚多。毕业后他又寄书法作品和书法名贴给我,但我仍旧不自知、不在意。甚至觉得他真是无事可做。那些他写过的书法作品大多零落,因为被随意放在了哪个角落,渐渐就忘记了。
喜欢书法是近一两年的事。忽然开了窍,而且喜欢得不行了。一发而不可收。于是想起爷爷和同学徐,珠泪滚滚的,根本忍不住。爷爷去世十年了,倘若活着……我与他一定秉烛夜谈,让他告诉我那些魏碑的好、杨凝式的简练、张旭有多狂、徐渭有多傻……
这真是定数。以为此生不会喜欢的事或者人,中年以来,那些低温的、稳妥的、空明的、独钓寒江的人或事物渐渐进入内心。不再慌张,不再讨好、强求,对于热烈或热闹的事物有着坚定的拒绝。
静影沉壁。清远深美。料峭独寒。习惯一个人独处时,是喜欢了一种生活方式。
早晨起来泡冻顶乌龙,之后是浓烈的大红袍,中午泡普洱,下午白茶,晚上太平猴魁收场。有时也喝金骏眉,间以花茶。佐以桂顺斋小点心。茶能收心,特别是一个人喝。有时也微醉——空腹喝时。爷爷和父亲喜欢喝浓茶,酽死人的那种,茶缸里有刻骨铭心的茶垢。印象中爷爷起来第一件事要喝茶,记不得他喝什么茶了,不会太名贵,父亲喝花茶,只喝花茶,张一元。高沫。每次回家给他称上二斤,喝不了几天就喝完了。太高档的茶他喝不了,刚下来的西湖龙井要一万块一斤,他说给他也喝不下,是喝钱呢。
家中亦有过了期的龙井和雀舌。绿茶。放不下身段似的,带着江南的虚张声势和恍惚。春天的时候喝它们,有一种恍惚。仿佛置身江南。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想念江南。它是一种存在。与我的气息谋合在一起。北方干冷的冬天清洌和凛凛,泡一壶龙井的时候会忆江南。

亦会煮粥。
粥是踏实的。平民似的踏实。今年我和小慧腌了很多的咸菜佐粥。十斤黄瓜,放上一斤的盐,泡一天一夜,把水控出来,黄瓜蔫了,像人收了心。然后放上一斤糖,半斤醋,再放上辣椒、生姜、蒜,四斤酱油,入腌菜坛,十日后便可食。
腌黄瓜脆、香、辣。和粥是天生一对的情侣。粥有时是小米粥加枣、杏仁,有时加南瓜,有时是白米粥,有时是黑米粥。各式各样的粥在冬天温暖着清凉的胃。有时喝粥太多就忘记吃主食,粥成了这个冬天的主人。喧宾夺主了。可是,那么好。
砂锅是路上买来的。推车卖砂锅的老人在廊坊到处走,一车的砂锅也卖不了几个钱,十几块钱一个。砂锅不精致,甚至潦草。买来煲汤自然是好的。有时候写着书法字贴,闻着砂锅里的气味冒出来,感觉光阴的老实和肯定。
中午的时候,日影照进来。老家俱都泛了光泽。每件老家俱都有故事。它们被我一一从市场上淘出来,然后搬到家里来。那个中药柜子写着很多中药名字,淡蓝色的颜色十分鬼魅。有时候坐在日影里一动不动,看着光影一点点落下去,落下去。那些日影多像是一个人的灵魂,四处游走,在这里与我合而为一。哦!那些雕琢,那些华丽,那些装饰,那些不必要,都没有了!甚至,那些文艺的小情小调,那些内心的纠缠与顽抗,它们悄然远去。只留下这这笃定、静默。是一幅老了的山水画,虽然黯淡了,可自有它的光泽与美意。
山水册子里,倪瓒的山水真空灵呀。钱选的梨花我看到的不是盛开,而是寂寥!还有沈周的山水,黄宾虹的浓墨,还有八大山上的空灵与绝孤、徐渭的疯狂……配上黄少华的声音,人书俱老,人声俱老。
姑姑来电话,让我陪她去老家上坟,给爷爷奶奶烧纸。之前总是她一个人去,这次我陪她去了。她跪在坟前,没有眼泪,只说:“爸爸妈妈,你们在天上要好好的,不要再吵了,我爸写字就让他写吧,给,这是给你们的钱”……纸钱烧起来……烟火极大。我亦没有眼泪,才想起爷爷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少,书法作品大多让他烧掉了,陪葬的是几只毛笔和一个用胶布缠着的收音机。只有一幅书法作品姑姑收藏着,上面写着:春和丽日无限好。我展开看时,居然准许自己落泪了!这前世今生,这独孤的少年与老年!这血缘,这因缘!
暖气烧得不太好。有些微冷。好友梁剑峰整个冬天只穿一条单裤。上面是一件短袖T恤和一个外罩。就这些了。然后还有一双球鞋。他有一种简洁与干净。四十岁男子少有的清澈与简单。他站在舞台上弹吉他或者唱京剧时像一株植物。我爱看他弹吉他,给弗拉门戈舞伴奏,吉他快疯掉了,那跳舞的女子也快疯掉了。而他似一株朴素的植物,淡淡的,永远散发着少年气息的植物。
多年来我只养一种植物:绿萝。撕几片放在水中,随便的一个容器就能养活它。刷牙的杯子、醉了一半的瓦罐、写着四季平安的民国老花瓶……家中全是绿萝。我只养绿萝。永远不会死的绿萝。一个人安静生长不惊扰任何人的绿萝。亲爱的绿萝。它们这样顽强,只要今生这样的美这样的好这样的寂静,蚀骨的寂寞之后是蚀骨的艳。剑峰说:要那么热干什么?凉一些,心里冷静。
还有裘裘。我们都喜欢叫他裘裘。有人介绍他是裘盛戎的孙子,在北京京剧院唱花脸。他不以为然。我喜欢他神情冷漠。不是装出来的冷漠。是那种永远温暖不起来的冷漠。
他喜欢戴帽子。各式各样的帽子。样子极像顾城。眼神那样忧郁。他唱戏时亦是那样的忧郁眼神。铜锤花脸是凛凛的神情,但他唱起来,居然也是哀伤的。
他还唱越人歌。声音在午夜像是一个人在唱经——心悦君兮君不知。他让我给他写这些灵歌。在一个法国音乐人家里,他和那个法国人唱得灵歌有致人于死地的快感。
有一天黄昏我们俩把车停在雍和宫附近。冬天的风大,红灯笼在旗杆上飘得好高,上面有个灯箱,写着三个字:京兆尹。我分外喜欢那三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吃饭的地方么?我问裘裘,不知道,他回答。但这三个字就够了,在北京的黄昏里,分外的诱人。说不出的气息与味道。
我们就在车子里发呆。发好长时间的呆。
去“小吊梨汤”吃饭,剑峰吃素。我没有说,其实也吃了好长时间素了。不想吃肉。一点也不想。说不出为什么。
偶尔也笑。笑得万籁俱寂。一个人发笑时更加动人。更为彻底的孤寂与美幻。电话早就关掉了。砂锅里的粥冒出成熟的味道,“一得阁”的墨汁还有一点点。外面的风更大了。黄少华的声音依旧苍桑的饱满。
下午的时光又醉又美。如果是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那些银行家两点要去青楼里打牌,四点吃点心,晚上八点吃青楼菜。那些青楼菜有着家常的温暖——黄鱼、带鱼、鲤鱼在上海是粗菜,青楼菜会做出它的端丽与细腻,那些青楼女子知道,留住男人的胃便留了男人的身。据说杜月笙请客,一桌青楼菜是一千大洋,外加二十根小金条。气派而有面子。但杜月笙最喜欢吃猪下水,这个习惯提示着他的出身。难得他喜欢戏,而且钟情于孟小冬。真好。我在下午要喝一碗红豆粥,或者泡一壶茶。一个人。
以为一天很长。就这样须臾之间过完。很快天黑下去,万籁俱寂的黑。新开路上的路灯灭了。雪光照进来,也白亮亮的。然后很快太阳升起,要泡一壶新茶了。
以为冬季很长,收敛了心性的一个季节,过得从容不迫。很快有了春的消息。不过须臾之间。
在这冬天,烟水飘袅的光阴里,清澈无尘的冬季,我一个人,忽尔盛开。盛大而隆重的绽开。我把光阴席卷而去了,你打开一看,哦,只是须臾。
——写于2013年深冬
原载2014年《北京文学》第7期。

本文节选自

《繁花不惊,银碗盛雪》
作者: 雪小禅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4-8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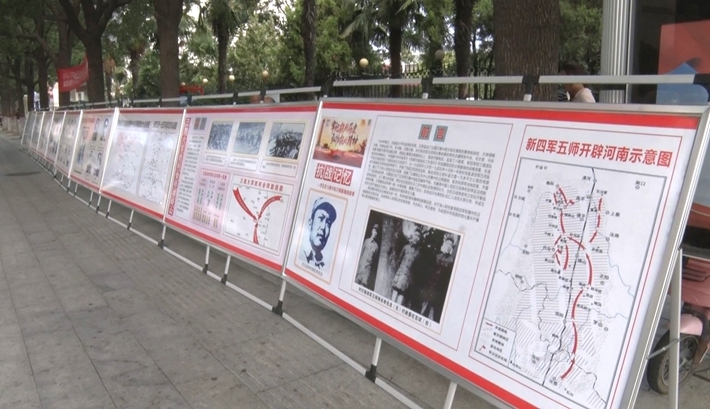







 豫公网安备 41172802000007号
豫公网安备 411728020000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