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划合作“头移植”手术的任晓平教授(右)和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卡纳维罗
【环球时报报记者 范凌志 】随着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近日宣布将与中国医生任晓平率领的医疗团队合作,计划于2017年底进行世界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人们对这个人类新创举既期待又充满疑惑。为彻底探究这个神秘的项目,《环球时报》9月18日专访哈尔滨医科大学手显微外科中心主任任晓平教授。在专访中,任晓平教授讲述了该计划的来龙去脉,并一再强调,这是一项重大的前沿课题,关系中国在现代医学中的地位,容不得半点马虎,他个人也反对利用这个话题进行炒作。
手部和面部移植成功,自然想到“异体头身重建术”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给这项手术命名为“异体头身重建术”?
任晓平:现在通俗的说法是“头移植”,是沿用传统的“器官移植”得来的,但这种说法不科学,容易误导人,因为头部不是一个器官。20世纪70年代,给猴子进行头部移植的美国医生罗伯特·怀特认为,应叫“身体移植”,但这种说法也没有被大家沿用。意大利的卡纳维罗医生将其命名为“天堂(HEAVEN)手术”,是“头部接合冒险手术”的缩写,但我认为这种叫法不太严谨,缺乏学术性。
我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参加学术活动时广泛征询临床、基础领域专家的意见,探讨之后提出“异体头身重建术”的命名方法,已经用了几年。这个名字我感觉比较合适,更科学,而且能说得清楚,且降低了手术的敏感性,毕竟“头移植”有时候听起来让人不舒服,而“异体头身重建术”就比较中性。
上个月,卡纳维罗医生来我这里时,我们探讨过命名问题。从事这项技术研究的人非常少,也就我们两个在牵头做。不过最后谁都没有说服对方,但达成一个共识:就像药物一样,这项技术应有个商品名和一个化学名或学术名,卡纳维罗医生的命名更像一个商品名,而我的命名方法则是一个学术名。具体命名能不能被人们接受,那要用时间来检验。
环球时报:您最早开始思考“异体头身重建术”是什么时候?
任晓平:已经有很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国外,那时国际医学界在挑战复合组织移植,“头部移植”是复合组织移植的最前沿,而我们要攻克的第一个复合组织就是手部。在路易斯维尔大学,我们启动了这一研究,花两年时间才完成临床前的实验,完成人类第一个手部移植手术,到现在也是存活时间最长的移植手。攻克手部移植后,面部移植自然就突破了,因为解决了免疫药物学方面的难题,这方面一突破,整个领域就带活了。现在,全世界各身体复合组织的移植零零散散已有200例左右。
做完手部和面部移植后,下一步的挑战自然就会想到头,不过这个想法并不新,无论从民间传说还是此前的科学界,都进行过探索和尝试,只不过上个世纪这项研究只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进入新世纪后,我们要用现代技术来认真从事这项研究。
环球时报:准备接受手术的俄罗斯志愿者斯皮里多诺夫患有先天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他认为“这项技术跟人类首次太空行走类似”。那么,您认为难在哪里?
任晓平:虽然在复合组织移植领域我们已有很好的经验,但头部移植必须要重新来。手部和面部移植确实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对头部中枢神经来说,不确定因素太多。
首先是缺血器官的损伤,传统的器官移植我们都会在有效的时间内尽快接上,心脏、肾脏等器官如果保存好了,几个小时内问题不大,手部两三天都有存活的。可是头部不行啊,太复杂,我们需要手术过后的人有正常的智商,但头部在室温情况下超过4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通血之后,很可能脑细胞已经坏死,这样就相当于手术失败。目前全世界还没对这一方面进行足够重视,很多非专业人士会把它简单化,一带而过。其实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第二个难点是免疫排斥反应,我的团队成员里有几位是专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这需要花几年时间来验证。
第三点是媒体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中枢,中枢难不难?难!重不重要?重要!但我要将它放到最后一位,因为它涉及术后身体有没有良好的功能,不影响近期的存活。我曾经表示,这个项目要分步走,第一步要有效解决缺血和免疫排斥问题,那么病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就能挽救他的生命,让他有良好的思维,这就算是个阶段性的成果。有了第一步的基础,第二步才是功能恢复,让接受手术者有一个生活质量。传统医学认为中枢神经不能恢复,但近十年的医学不断发展,这个结论几乎要被推翻,不论科学研究还是临床,都有很好的实例。这个项目很有希望,但这个希望一定要建立在良好的科研基础上,项目所需的人力物力非常大,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具体做不做,在哪里做,取决于国家和法律”
环球时报:愿意提供身体的人是“脑死亡但其他部位健康的捐献者”。这样的捐献者好找吗?对人种有要求吗?“换头”之后,人会有哪些变化?
任晓平:当然,捐献身体有一个匹配的问题,先不说种族分型、血液分型,单从相貌上,如果一个黑人头部接到一个白人身体上,或者体毛少的与体毛浓密的接在一起,肯定不合适。从医学角度,我们会从血型上、组织学配型上寻找最接近的匹配方,以减少术后的排斥反应。
至于手术后的变化,我认为,常规手术都可能会让患者产生一些心理变化。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手术,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人的属性不会变,中枢神经的思想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和换肾、换肝一样,我们可以把身体当成一个复合组织器官,只不过这个组织器官大一些,只是量上的变化。另外,这样一个项目会配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帮他疏导,来度过危险期。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这个手术在医学、法律、伦理等领域引发的巨大争议?
任晓平:手术真的要做,也不会一两个科学家说做就做。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就是为了让技术达到最佳。具体做不做,在哪里做,取决于国家、法律,这是相关部门来探讨的事情。但作为医生,我认为,新生事物都会存在争议。以我粗浅的理解,伦理学是个行为规范科学,面对病人的生命,伦理学必须要让步。如果一个技术可以有效延长人的生命,伦理学角度没有理由不批准。对于新事物,伦理学可以制定一个规范,让新技术在这个框架以内进行,但没有道理阻碍科学的发展。我认为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个基础上,伦理学的一些规范可以帮助临床实践。
“头移植”是天大的难题,但中国科学家不应回避
环球时报:卡纳维罗近日表示,您是“全世界唯一能领导这个项目的人”。他是怎么和您确定合作的?
任晓平:去年卡纳维罗先生给我发电邮说:“我读到你的文章,你现在做的工作我很感兴趣,我们能不能联合?”他应该是检索到我之前的文章,了解我已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跟他的研究很符合,所以才联系我。
卡纳维罗的话可能有恭维的意思,但也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科研力量的向往。对比我20年前出国时国内外科研环境发生的变化,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吸引更多外国学者的关注。
环球时报:所以,您认为“异体头身重建术”对中国的科研有特殊意义?
任晓平:我们国家是年轻的巨人,充满生机,但也有需要进步的地方。我们国家过去在现代医学缺少领先的领域,我们都是跟着外国做,创新很难,风险也大。“头移植”更是天大的难题,在这方面虽然存在争议,但科学家不应回避,这是一项严肃的课题、一个重大的前沿,不能当成儿戏来炒作。当然,一个科学家的力量太有限了,没有资金寸步难行,希望国家层面能重点扶持,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为现代医学作贡献的重要契机。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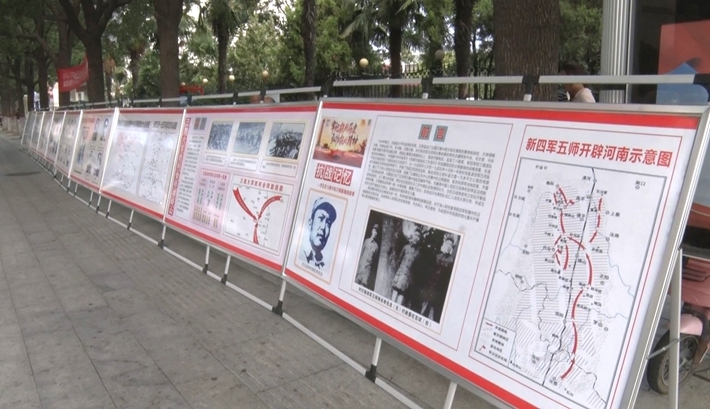







 豫公网安备 41172802000007号
豫公网安备 41172802000007号